导读:上周去苏州会友,在诚品书店碰到本台湾人校对的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虽然我已经有两个版本的这书了,还是果断入手了一本,老张同志的书写的还是很赞的,特别实用,前几年我特别喜欢翻。
如果没有读过老张的书,很多中医人对于老张的印象应该是停留在一年级时候中医基础理论讲清末民国初年中西医结合的典范张锡纯,用阿司匹林配石膏解热的例子。其实老张同志的贡献及才华远不止这个啊,老张同志的书可以细细品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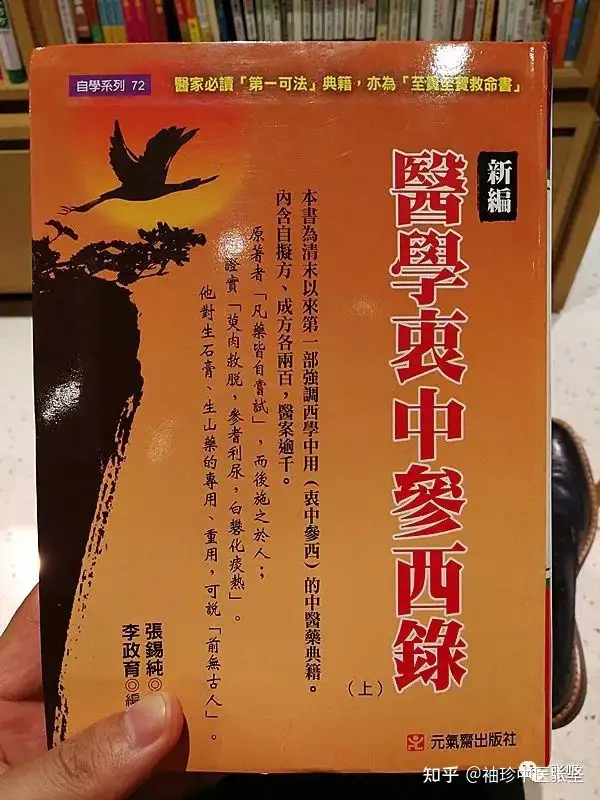
张锡纯用药经验管窥———兼谈去性存用之法
老张同志的很多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老张同志在药性解部分写到一味我们男科常用药:粉萆薢。老张说萆薢味淡而温,能直趋膀胱温补下焦气化,治小儿夜睡遗尿,或大人小便频数,致大便干燥,其温补之性,兼能涩精秘气,患淋证者禁用。后来又强调了一遍,萆薢为治失溺要药不可用于治淋。
但是程氏萆薢分清饮的名气太大咯,大家都用他来治淋证,尤其是膏淋,就是小便混浊像淘米水一样的那个淋,老张同志还举了个例子,他们老家隔壁村的,有个人得了淋证,类似尿路感染,请了个中医来就给他用了萆薢分清饮,两剂一喝小便小不出来了。我搞男科碰到这种尿频的患者比较多,体会也比较深,确实是像老张同志说的那样,尿频、夜尿多的都可以用,明明是个固涩药,效果还是不错。
我也犯过老张同志说的那个错误,曾治一人,前列腺炎尿频,舌根厚腻,湿胜明显,夜尿比较多,总要起夜,有点像实证:淋,不是虚症的膀胱肾气化气无力的尿频,结果给他用了粉萆薢以后,就一剂第二天那个患者就找我,问我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夜里依旧要起夜想小便,但是平时能小出来,吃了你的药,光有尿意,小不出来。我的心里立马想到了两件事:①抓的这个药材质量还不错,真货。②老张写的东西实实在在,诚如他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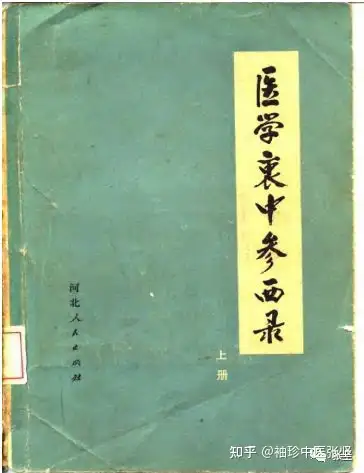
(最喜欢这个1972年出的,带毛主席语录的版本)
比如2:老张同志创立了一个治疗阴虚劳热的方子,十全育真汤,人参4钱、生黄芪4钱、生山药4钱、知母4钱、玄参4钱,生龙骨4钱,生牡蛎4钱,丹参2钱,三棱1钱半,莪术1钱半。
这个方子看着有点奇怪,治虚劳补就补勒,用什么三棱莪术,活血破血干嘛?感觉很突兀,老张同志自己解释了:我这个是学的仲景《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看仲景那意思就是虚劳者必然血痹,血痹特别厉害的没有不虚的,痹就是痹阻不通的意思,都说虚症不能用破血药,但是要分情况,既然虚劳都有血痹,那么治血痹就是治虚劳,仲景本人艺高人胆大,大黄蛰虫丸、百劳丸用的都是大黄、干漆、水蛭等猛药,相比之下三棱、莪术就弱爆了。但是用这些破血药是有条件的,要配伍补药,与参、术、芪并用。
老张同志还在后面写了一句个人经验:三棱、莪术与参、术、芪诸药并用,大能开胃进食,愚屡试屡效。
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估计也是学习了老张的参西录,也看到了这句话,朱老在书中《朱良春用药经验集》第41篇写了个专题:黄芪配莪术治慢性胃炎,消癥瘕积聚。有兴趣的自己去翻阅,朱老提到了很多人,也有老张,但说的不是这一篇。老张同志这里说的虚劳皆血痹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想想肿瘤晚期患者的高凝状态,还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这个方子反映的特别和独到之处,还不止上面的说到的三棱、莪术配补药。还有这个黄芪配知母,老张同志说,王叔和写脉法时说:脉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也不一定,他平时碰到这种虚劳发热脉数明显的,只要还有点根(肾气),重用黄芪、知母莫不随手奏效。黄芪温升补气,知母寒润滋阴,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一个温药,一个寒药,两个一块用到底是显热还是显凉?这个也是我常说的,首辨寒热,明显寒症你用那么多凉药肯定不合适,寒热并用可以,最后方子组合起来肯定要偏热才对。老张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还经过了长期的临床观察:又(我)尝权衡黄芪之热力,与知母之寒力,亦无轩轾,等分用之可久服无寒热也,此论汤剂,作丸剂可知知母寒力胜于黄芪热力。(意思是我考量了,如果入汤剂黄芪和知母寒热几乎对等1:1,如果入丸剂,知母寒力要比黄芪热力强一点)
我之所以极力推崇老张同志的书,因为真的很棒,思考的问题很实在,也做了大量的临床观察,还分汤剂和丸剂。正如他自己所说:临证调方者,务须细心斟酌,随时体验,息息与病机相符,而后百用无一失也。
老张有了这一临床体会,是用来服务临床的,让粗糙的中医搞的更精细一点,后面对于大气下陷证,老张同志立了个升陷汤:(生黄芪6钱,知母3钱,柴胡1钱半,桔梗1钱半,升麻1钱),老张同志说,升陷者黄芪为主,因黄芪既善补气,又善升气,惟其性稍热,故以知母凉润济之。这里就是用到了前面的实践调研经验,知母能制约黄芪的热力,方子微温就不要等量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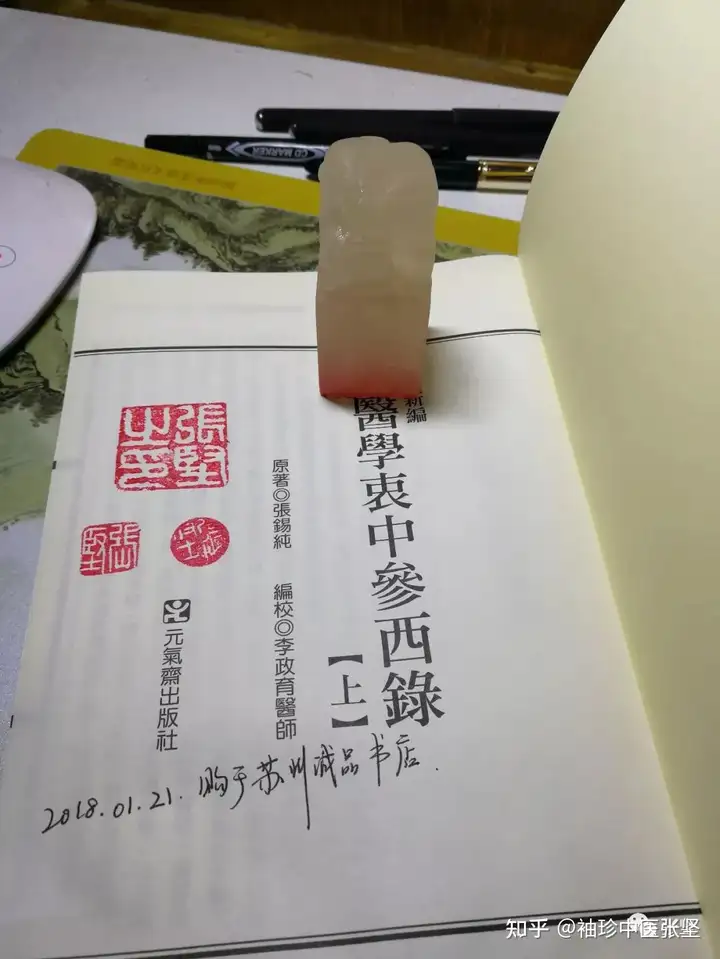
老张同志这一招黄芪配知母,加上前面那个三棱、莪术配参、术、芪。其实是方剂学里面一种高明的配伍方式,叫去性存用。中药跟人一样,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叫做偏性,就是有脾气,很多时候想用他的长度,又怕被短处所掣肘,这个时候挑一个助手就非常有讲究了,不光要弥补他的短处,还能在长处上有所帮助,两全其美。这个就看派兵遣将的水平了。光制约短处,于治疗大方向无益,那只能算一般选手。
中药的炮制也是去性存用的一种,前面写的那篇煮大方如烹小鲜———解读《脾胃论》系列讲东垣碰到一个上热下寒的病人,想用黄芩、黄柏、生地去清热,又觉太寒,于是想出用酒炒黄芩、黄柏,即可以制约部分寒凉之性,还可以乘着酒性上行,达到清上焦热的目的。可见东垣也是善用去性存用这种方法的人。

(仙林仲景像)
老张同志的很多套路是跟我们老张家的另外一个名人学的,那就是张仲景,仲景是最擅长用这个寒热搭配,去性存用的医家,比如那个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疗无寒邪郁表的肺热壅胜喘证,仲景擅长用麻黄配杏仁这种一宣一降的套路,但是本来就热,还用麻黄怎么好?这不是抱薪救火么?于是仲景又用了个石膏,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那些个泻心汤黄连黄芩和干姜的配伍都是这个意思。
丹溪的名方左金丸,黄连配吴茱萸也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高人出手也都有一些类似的套路。哈哈哈,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套路,我喜欢用这个大辛大热的吴茱萸治疗肝系的一些问题,寒症无话可说,热证想用就配伍个专入肝经,性凉的赤芍。这两个也差不多,基本上6g吴茱萸对10g赤芍,吃进去感觉不到特别的热或者寒。
(完)
本文转自知乎,原文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513230996
 修元健康网
修元健康网